
就在功利主义成型的那个世纪接近尾声时,伊曼努尔·康德激烈批判了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作为丰富的正义理念来源选择之一的功利主义。康德和基于功利主义的正义概念的拥护者一样,全身心地接受人类拥有平等价值这一说法。但是从其他基本角度来讲,他与休谟及其继承者的想法不同。最重要的是,康德明显反对人类享受或者幸福的提升能够一直作为合理的正义理念的基础这一假设。对康德来说,关于人类的基本真相是人类是自由的、理性的、负责的代理人,这个真相与关于正义的考虑有关。最先和最早的功利主义者不否认人类是(至少有可能成为)自由理性的生物。但是,这种特性并不属于这些哲学家的正义理念的基础。反而对康德而言,人类是(潜在地)自由的、理性的和负责这一假说是所有合理的整体正义和道德理念的基础。
康德在他的著名论文“理论和实践”中举的一个例证是他区别于将功利主义概念作为正义理念基础的人的象征。想象一下这样一种情况,有人被任命为一大笔财产的受托人,而财产的主人已去世,财产的继承人虽然拥有独立的财富,却挥霍浪费又尖酸刻薄,且他们并不知道财产的存在。如果受托人和他的家庭,即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遭遇严重的财政危机,而这笔个人财产的财富足以解决他们的困苦。那么假设受托人将这笔财产挪为己用,如果他选择这么做,他的盗用行为也永远不会被财产继承人或者其他人得知。很显然,在这个设想中,考虑到所有财产继承人和受托人自己家庭成员的现状,该受托人如果隐瞒继承人关于财产的消息,并盗用财产解决自家的困苦,那么就可提升相关人员的集体幸福。他甚至只采取了最轻微的手段,却能够大幅提升家庭成员的幸福,又不影响财产继承人的幸福。但是康德认为这种盗用是错误的行为。受托人有责任根据去世财产主人的意愿分配财产,把财产传递给任何其他人而非真正的财产继承人均算为渎职。(要注意,在康德的逻辑中,就算以接受财产份额来减轻痛苦的赤贫者对受托人而言仅仅是个陌生人,结论依旧不变。)虽然可能有强烈的情感促使从既定的受益者手中转移相关的资源以减轻人们的痛苦,但是康德争论说,按财产原主人的意愿分配财产是受托人的责任,这个责任应该超越为了提升幸福而转移财产的诱惑。简洁概括这个观点就是,对康德而言,正确的比有益的(在伦理上或道德上)优先考虑。
1781年,康德发表《纯粹理性批判》,奠定了他伟大的现代哲学家之一的名声。紧跟着的是他主要的道德政治哲学作品,包括1785年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及1797年达到顶峰的《道德形而上学》。在康德潜心写作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他详细说明并完善了自己的论点。我的讨论首要的基础是康德18世纪90年代的作品,包括他在1793年创作的关于“理论与实践”的论文和在1795年创作的关于“永久和平”的论文,以及《道德形而上学》。
康德不断引证两个论据来反驳功利主义可恰当地作为论证道德和正义的基础这一说法。首先,我们从功利主义背景推理出的任何结论都可能具不确定的。这是上述受托人责任那个例子的核心要点。康德争论说,受托人如果根据功利主义结果决定如何处理财产,那么他会被迫评估所有处理方案(例如一次性完全占有财产后再慢慢使用,或者将这笔财产分配给所有继承人,希望以此加强自己的名声,最终获得财政利益)可能会产生的结果。当然,这么做具有不确定性,只会导致受托人无法得到明确的道德指导。相反,康德认为,如果受托人选择按(康德认为的)责任要求进行操作,就不会对何为正确的行为产生任何怀疑。他认为,即使是一个八九岁的小孩也能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应依照自己的责任。
其次,康德争论说一个扎实的道德理论不能以幸福为基础,因为幸福的来源因人而异,只有个人喜好最适合决定如何以最佳的方式追求他或者她的幸福。人们必须根据自己的经历明确什么能带给自己快乐,当然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在幸福的基础上无法得出通用(或者至少是普遍的)道德结论,而且在康德看来,道德戒律必须是自然而然且普遍通用的,它以相同的方式指导每个人,并不考虑因人而异的个人喜好。此外,康德认为允许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幸福并没有错,强加给人类任何特定的幸福概念都是不对的。他似乎认为功利主义方式的特征就是试图用这样的方法来强加幸福。
上述论点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第一个论点假设不存在真正的道德责任冲突。因为如果存在这些冲突,康德设想的责任感有时无法就一个人的正确行为得出明确的结论。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康德责任教条对于功利主义推理的优势就会消失,因为用前者的方法推理出的道德结论和后者一样不确定。但是康德提出的不存在真正的道德责任冲突的假设似乎有些牵强。借用他自己举的例子来说:假设一个遭受海难的人抓住一块木板以防自己溺水,而另一个幸存者和前者一样,已经筋疲力尽,如果没有支持物维持漂浮,他就会溺水而死,他同样也抓住了那块木板。不幸的是,那块木板只能支撑他们其中一人。康德的观点是,第一个幸存者如果为了使自己活命而推开第二个幸存者,这是不对的行为。他的理由是,对他而言,不剥夺没有对自己造成伤害的人的性命是“绝对责任”,而维持自己的生命只是“相对责任”。换句话说,只有在我不会犯罪的前提下才有义务确保自己的生命,所以才说这是相对的责任。而康德似乎认为将第二个受害者推离木板这个行为本身就是犯罪。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康德的结论是正确的。当两者中只有其一可以幸存时,为什么拯救自己性命的责任不能同等于不剥夺别人性命的责任呢?用这个例子总结存在真正的道德责任冲突似乎更有说服力。而康德得出相反结论的理由似乎是他坚决认为他的道德教条应该排除所有会造成道德歧义的可能性,虽然这种排除的基础在有些情况下并没有那么有说服力。
他的第二个论点也有问题,部分原因是这个论点合并了道德原则和政策建议,前者按理说应该(在康德的观点里就是必须)是明确的,而后者就其本质而言经常是不明确的(因此康德才要进行讨论)。还有部分原因是这个论点建立在对功利主义的误解之上。如我们所见,那些拥护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正义概念的人意识到幸福的源头因人而异。这种认知是边沁提出的“奇特的”价值观的关键点,也是休谟、边沁和很多类似的思想家所提倡的政策的基础。根据这种认知可以得出,我们无法将从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正义概念中得出的政策建议调整到我们确定的将最大化集体功利的程度。即使没有其他阻碍,也很难落实实现这个目标所需的详细信息的数量。功利主义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应是支持能够增加个人所享用的机会和资源的法律和政策,如此一来,他们就可利用这些优势来追求自己的幸福,通常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这一回应也有效地削弱了康德的第二个论点,该论点的基础似乎是律法和政策的功利主义理论规定了要强加特殊类型的幸福这一猜想。就像康德认为的那样,功利主义思想家拥护的,至少边沁拥护的道德原则是很明确的,即使源自这些原则的政策建议并非总是明确的。因此,边沁也被认为是首个全面系统地表述功利主义的代表。对于用自己的方式追求幸福的个人而言,这些道德原则留出了足够的空间。
(本文节选自《正义简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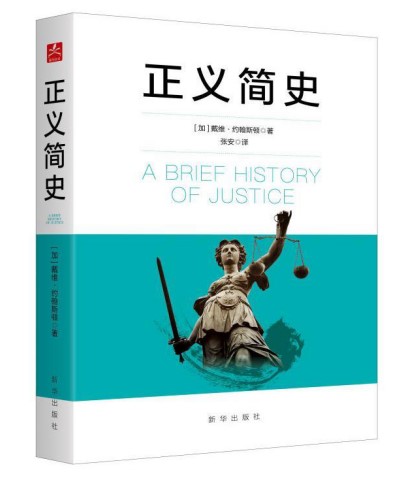
《正义简史》
ISBN 978-7-5166-4286-3
戴维·约翰斯顿 著
新华出版社 2018年9月
定价:48.00元